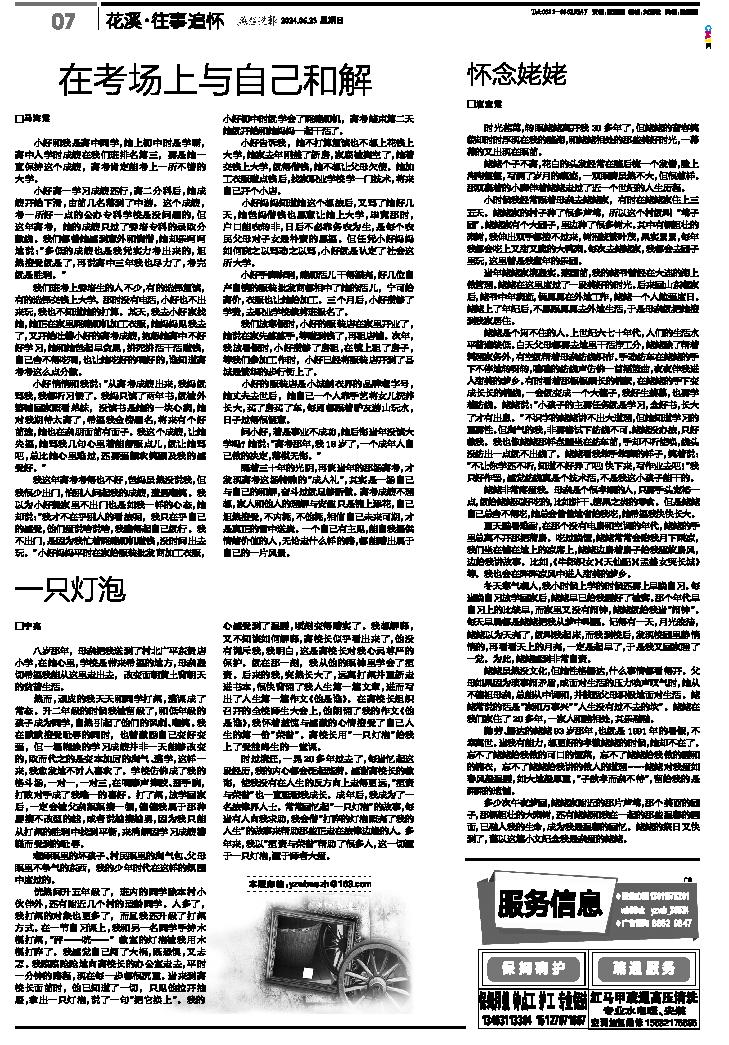□袁宝霞
时光荏苒,转眼姥姥离开我30多年了,但姥姥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,和姥姥相处的那些美好时光,一幕幕的又出现在眼前。
姥姥个子不高,花白的头发经常在脑后梳一个发髻,脸上沟沟壑壑,写满了岁月的痕迹,一双眼睛虽然不大,但很慈祥。那双裹着的小脚伴着姥姥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。
小时候我经常跟着母亲去姥姥家,有时在姥姥家住上三五天。姥姥家的村子种了很多芦苇,所以这个村就叫“苇子园”。姥姥家有个大园子,里边种了很多树木。其中有棵粗壮的梨树,我伸出双手都搂不过来,树冠枝繁叶茂,果实累累,每年我都会吃上又甜又脆的大鸭梨。每次去姥姥家,我都会去园子里玩,这里曾是我童年的乐园。
当年姥姥家境殷实。建国前,我的姥爷曾经在大连的海上做管理。姥姥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后来回山东老家后,姥爷中年病逝,俩舅舅在外地工作,姥姥一个人勉强度日。姥姥上了年纪后,不愿跟舅舅去外地生活,于是母亲就把她接到我家居住。
姥姥是个闲不住的人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。白天父母都要去地里干活挣工分,姥姥除了帮着料理家务外,有空就帮着母亲纺线织布。手动纺车在姥姥的手下不停地转呀转,嗡嗡的纺线声仿佛一首摇篮曲,夜夜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。有时看着那根根细长的棉絮,在姥姥的手下变成长长的棉线,一会就变成一个大穗子,我好生羡慕,也要学着纺线。姥姥说:“小孩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,念好书,长大了才有出息。”不识字的姥姥讲不出大道理,但她知道学习的重要性。但淘气的我,非要尝试下纺线不可。姥姥没办法,只好教我。我也像姥姥那样盘腿坐在纺车前,手却不听使唤,线头没纺出一点就不出线了。姥姥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子,笑着说:“不让你学还不听,知道不好弄了吧!快下来,写作业去吧!”我只好作罢,感觉纺线真是个技术活,不是我这小孩子能干的。
姥姥非常疼爱我。母亲是个很孝顺的人,只要手头宽裕一点,就给姥姥买好吃的,比如饼干、糖果之类的零食。但是姥姥自己总舍不得吃,她总会偷偷地省给我吃,她希望我快快长大。
夏天酷暑难耐,在那个没有电扇和空调的年代,姥姥的手里总离不开那把蒲扇。吃过晚饭,姥姥常常会陪我月下乘凉,我们坐在铺在地上的凉席上,姥姥边扇着扇子给我驱蚊扇风,边给我讲故事。比如,《牛郎织女》《天仙配》《孟姜女哭长城》等。我也会在阵阵凉风中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冬天寒气袭人,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还要上早晚自习。每当晚自习放学回家后,姥姥早已给我暖好了被窝。那个年代早自习上的比较早,而家里又没有闹钟,姥姥就给我当“闹钟”。每天早晨都是姥姥把我从梦中叫醒。记得有一天,月光皎洁,姥姥以为天亮了,就叫我起床,而我到校后,发现校园里静悄悄的,再看看天上的月亮,一定是起早了,于是我又回家睡了一觉。为此,姥姥感到非常自责。
姥姥虽然没文化,但她性格豁达,什么事情都看得开。父母如果因为琐事闹矛盾,或面对生活的压力唉声叹气时,她从不偏袒母亲,总能从中调和,并鼓励父母积极地面对生活。姥姥常说的话是“家和万事兴”“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”。姥姥在我们家住了20多年,一家人和睦相处,其乐融融。
勤劳、豁达的姥姥93岁那年,也就是1991年的暑假,不幸离世。当我有能力,想更好的孝敬姥姥的时候,她却不在了。忘不了姥姥给我做的可口的饭菜,忘不了姥姥给我做的暖和的棉衣,忘不了姥姥给我讲的做人的道理……姥姥对我爱如春风般温暖,如大地般厚重,“子欲孝而亲不待”,留给我的是深深的遗憾。
多少次午夜梦回,姥姥家附近的那片芦苇,那个美丽的园子,那棵粗壮的大梨树,还有姥姥和我在一起的那些温馨的画面,已融入我的生命,成为我最温馨的回忆。姥姥的祭日又快到了,谨以这篇小文纪念我最亲爱的姥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