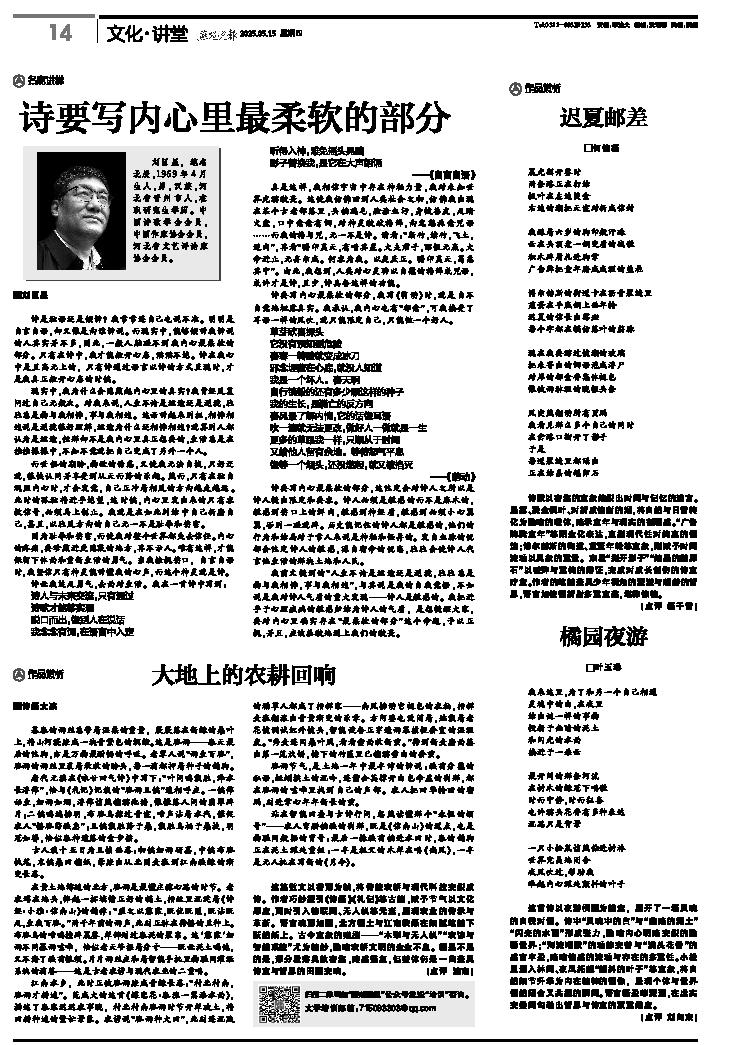■诗经女孩
暮春的雨丝总带着温柔的重量,簌簌落在新绿的桑叶上,将山河浸染成一块青黛色的绸缎。这是谷雨——春天最后的注脚,亦是万物最酣畅的呼吸。老辈人说“雨生百谷”,谷雨的雨丝里裹着秋收的盼头,每一滴都押着种子的韵脚。
唐代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》中写下:“叶间鸣戴胜,泽水长浮萍”,恰与《礼记》记载的“谷雨三候”遥相呼应。一候萍始生,细雨如烟,浮萍悄然铺满池塘,像撒落人间的翡翠碎片;二候鸣鸠拂羽,布谷鸟掠过青空,啼声沾着水汽,催促农人“播谷莳秧急”;三候戴胜降于桑,戴胜鸟栖于桑枝,羽冠如簪,恰似春神遗落的金步摇。
古人裁十五日为三帧画卷:初候细雨研墨,中候布谷执笔,末候桑田铺纸,晕染出从北国麦浪到江南秧绿的渐变长卷。
在黄土地绵延的北方,谷雨是最懂庄稼心思的时节。老农蹲在地头,捧起一抔墒情正好的褐土,指纹里沉淀着《诗经·小雅·信南山》的韵律:“益之以霡霂,既优既渥,既沾既足,生我百谷。”两千年前的雨声,此刻正淋在待播的豆种上。布谷鸟的啼鸣撞碎晨雾,犁铧划过春泥的裂帛。这‘霡霂’细雨不同暴雨喧哗,恰似老天爷握着分寸——既让泥土喝饱,又不淹了秧苗根须。片片雨丝应和着智能手机里物联网灌溉系统的滴答——这是古老农谚与现代农业的二重唱。
江南水乡,此时正被谷雨染成青绿长卷:“村北村南,谷雨才耕遍”。范成大的这首《蝶恋花·春涨一篙添水面》,描述了春寒迟迟农事晚,村北村南谷雨时节开犁破土,将田耕种遍的繁忙景象。农谚说“谷雨种大田”,此刻连沉默的稻草人都成了指挥家——南风拂动它褪色的衣袖,指挥麦浪翻滚出青黄渐变的乐章。方阿婆也没闲着,她戴着老花镜调试红外镜头,智能设备正穿透雨幕捕捉蚕室的温湿度。“秀麦连冈桑叶贱,看看尝面收新茧。”待到新麦磨面蒸出第一笼炊饼,檐下的竹匾里已铺满雪白的蚕茧。
谷雨节气,是土地一年中最丰沛的诉说:秧苗分蘖的私语,蚯蚓拱土的沉吟,连蒲公英撑开白色伞盖的刹那,都在谷雨的喧哗里找到自己的声部。农人把四季轮回的密码,刻进掌心年年新长的茧。
站在智能田垄与古诗行间,忽然读懂那个“永恒的顿号”——农人弯腰插秧的刹那,既是《信南山》的逗点,也是物联网数据的冒号:最后一株秧苗插进水田时,春的韵脚正在泥土深处重组:一半是祖父的木犁在唱《豳风》,一半是无人机在写新的《月令》。
这篇散文以谷雨为轴,将传统农耕与现代科技交织成诗。作者巧妙援引《诗经》《礼记》等古籍,赋予节气以文化厚度,同时引入物联网、无人机等元素,展现农业的传承与革新。语言瑰丽如画,北方褐土与江南秧绿在细腻笔触下跃然纸上。古今意象的碰撞——“木犁与无人机”“农谚与智能系统”尤为精妙,隐喻农耕文明的生生不息。稍显不足的是,部分段落典故密集,略感繁复,但整体仍是一曲兼具诗意与哲思的田园交响。(点评 潼南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