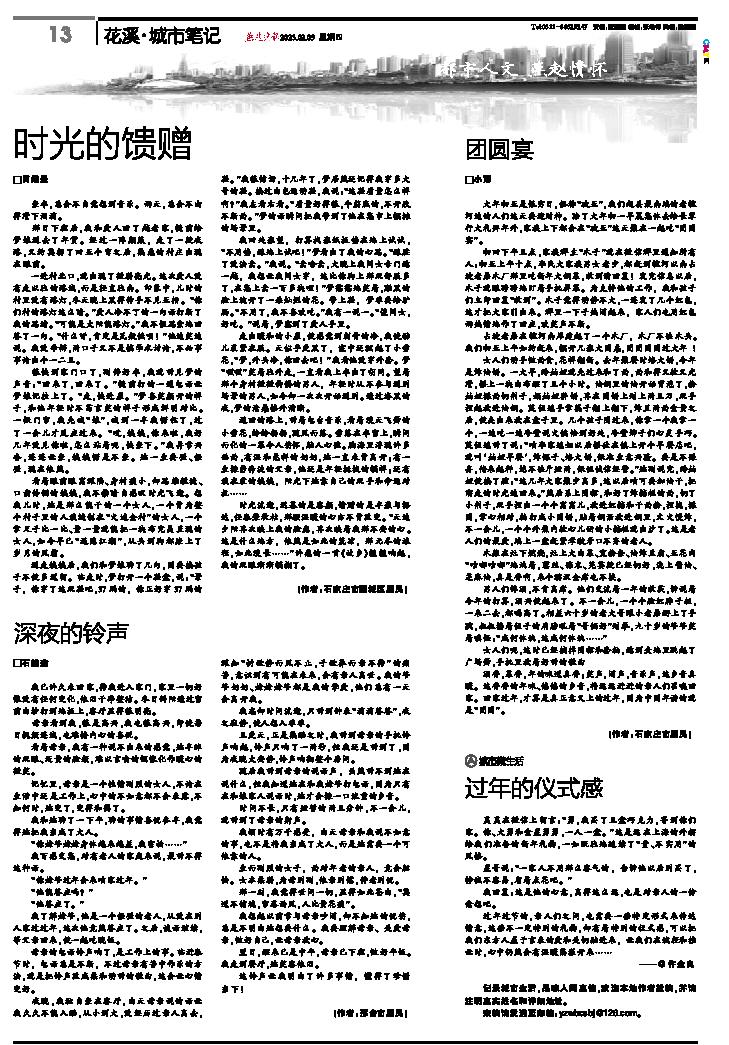□肖维景
坐车,总会不自觉想到音乐。雨天,总会不由得滑下泪滴。
那日下班后,我和爱人回了趟老家,提前给爹娘送去了年货。经过一阵颠簸,走了一段夜路,又约莫拐了四五个弯之后,熟悉的村庄出现在眼前。
一进村北口,就出现了微弱亮光。这次爱人没有走以往的路线,而是径直往南。印象中,儿时的村里没有路灯,冬天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“你们村的路灯这么暗。”爱人冷不丁的一句话打断了我的思绪。“可能是太阳能路灯。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一句。“什么呀,肯定是瓦数低呗!”他边笑边说。我没争辩,两口子又不是搞学术讨论,不必事事论出个一二三。
很快到家门口了,刚停好车,我就听见爹的声音:“回来了,回来了。”提前打的一通电话让爹娘记挂上了。“走,快进屋。”爹喜笑颜开的样子,和他年轻时不苟言笑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。一掀门帘,我先喊“娘”,喊到一半我愣住了,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“哎,姨姨,你来啦,我好几年没见你啦,怎么站着呢,快坐下。”我异常兴奋,连连让坐,姨姨愣是不坐。她一生要强、倔强,现在依然。
看着眼前眼窝深陷、身材瘦小,却思维敏捷、口齿伶俐的姨姨,我不禁暗自感叹时光飞逝。想我儿时,她是那么能干的一个女人,一个曾为整个村子里的人裁缝制衣“火遍全村”的女人,一个拿尺子比一比、量一量就能把一块布完美呈现的女人,如今早已“退隐江湖”,从头到脚都染上了岁月的风霜。
送走姨姨后,我们和爹娘聊了几句,因要接孩子不便多逗留。临走时,爹打开一个鞋盒,说:“景子,你穿了这双鞋吧,37码的,你正好穿37码的鞋。”我很惊讶,十几年了,爹居然还记得我穿多大号的鞋。接过白色运动鞋,我说:“这鞋质量怎么样啊?”我左看右看。“质量好得很,牛筋底的,不开胶不断面。”爹的话瞬间把我带到了他在集市上摆摊的场景里。
我四处张望,打算找张纸板垫在地上试试,“不用垫,踩地上试吧!”爹看出了我的心思。“踩脏了没法卖。”我说。“卖啥卖,大晚上我闺女专门跑一趟,我想让我闺女穿,这比你脚上那双舒服多了,在集上卖一百多块哩!”爹憨憨地笑着,黝黑的脸上绽开了一朵灿烂的花。带上鞋,爹非要给驴肠。“不用了,我不喜欢吃。”我有一说一。“傻闺女,好吃。”说着,爹塞到了爱人手里。
走出暖和的小屋,便感觉到刺骨的冷,我使劲儿裹紧衣服。天似乎更黑了,空中还飘起了小雪花,“爹,外头冷,你回去吧!”我看他没穿外套。爹“嘿嘿”笑着往外走,一直看我上车出了胡同。望着那个身材微微佝偻的男人,年轻时从不参与送别场景的男人,如今却一次次开始送别。透过漆黑的夜,爹的沧桑格外清晰。
返回的路上,听着电台音乐,看着漫天飞舞的小雪花,纷纷扬扬,随风而落。雪落在车窗上,瞬间而化的一幕令人伤怀,触人心弦。脑海里浮现许多画面,有温和慈祥的奶奶,她一直未曾离开;有一生操劳奔波的父亲,他还是年轻挺拔的模样;还有裁衣裳的姨姨,阳光下她靠自己的双手和命运对抗……
时光流逝,迟暮的是容颜,馈赠的是丰盈与豁达,任春荣秋枯,那颗温暖的心亦不曾改变。“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,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。这是什么地方,依然是如此的荒凉,那无尽的旅程,如此漫长……”许巍的一首《故乡》缓缓响起,我的双眼渐渐模糊了。
(作者:石家庄市藁城区居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