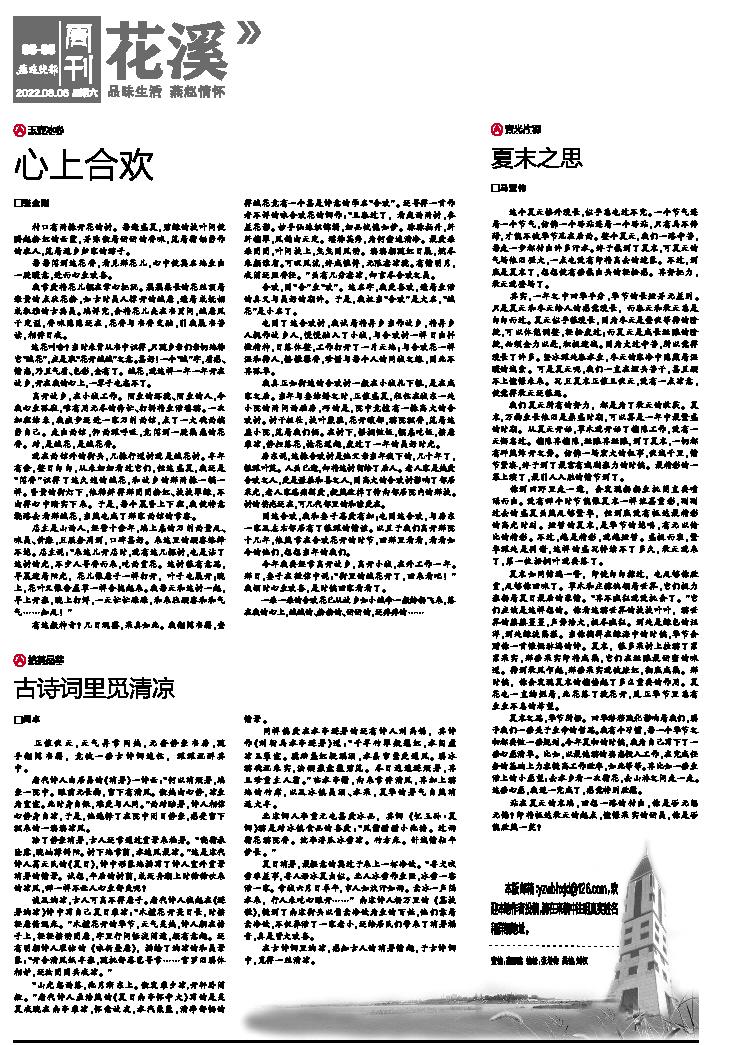□张金刚
村口有两株开花的树。每逢盛夏,碧绿的枝叶间便腾起粉红的云霞,并弥散着甜甜的香味,笼着荷锄劳作的农人,笼着返乡归家的游子。
每每闻到这花香,看见那花儿,心中便莫名地生出一股暖意,进而心生欢喜。
我常爱将花儿摆在掌心把玩。簇簇柔长的花丝顶着嫩黄的点状花粉,如古时美人撑开的绒扇,透着或妩媚或淑雅的古典美。端详完,会将花儿夹在书页间,绒扇风干定型,香味隐隐还在,花香与书香交融,引我展书苦读,相伴日夜。
这花叫啥?当时未曾从书中识得,只随乡亲们亲切地称它“绒花”,应是取“花开绒绒”之意。甚好!一个“绒”字,质感、情态,乃至气质、色彩,全有了。绒花,就这样一年一年开在故乡,开在我的心上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离开故乡,在小城工作。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,令我心生孤寂,唯有用无尽的奔忙、打拼将生活填满。一次加班结束,我疾步迈进一家刀削面馆,点了一大碗面犒劳自己。走出面馆,仰面深呼吸,竟闻到一股熟悉的花香。对,是绒花,是绒花香。
就在面馆外的街头,几株行道树就是绒花树。半年有余,整日匆匆,从未细细看过它们,但这盛夏,我还是“闻香”识得了这久违的绒花,和故乡的那两株一模一样。昏黄的街灯下,依稀辨得那团团粉红、枝枝翠绿,不由得心中踏实下来。于是,每个晨昏上下班,我便特意绕路去看那绒花,当然也成了那家面馆的常客。
店主是山西人,经营十余年,端上桌的刀削面量足、味美、价廉,且服务周到,口碑甚好。来这里的顾客络绎不绝。店主说:“来这儿开店时,就有这几棵树,也是沾了这树的光,不少人寻香而来,吃面赏花。这树很有意思,早晨迎着阳光,花儿像扇子一样打开,叶子也展开;晚上,花叶又像含羞草一样合拢起来。我每天和这树一起,早上开张,晚上打烊,一天忙忙碌碌,和来往顾客和和气气……知足!”
有这般神奇?几日观察,果真如此。我翻阅书籍,查得绒花竟有一个甚是诗意的学名“合欢”。还寻得一首作者不详的咏合欢花的词作:“三春过了,看庭西两树,参差花影。妙手仙姝织锦绣,细品恍惚如梦。脉脉抽丹,纤纤铺翠,风韵由天定。堪称英秀,为何尝遍清冷。最爱朵朵团团,叶间枝上,曳曳因风动。缕缕朝随红日展,燃尽朱颜谁省。可叹风流,终成憔悴,无限凄凉境。有情明月,夜阑还照香径。”虽有几分凄凉,却言尽合欢之美。
合欢,因“合”生“欢”。这名字,我更喜欢,透着生活的真义与美好的期许。于是,我权当“合欢”是大名,“绒花”是小名了。
也因了这合欢树,我试着将异乡当作故乡,将异乡人视作故乡人,慢慢融入了小城,与合欢树一样日出抖擞精神,日落休整,工作打开了一片天地;与合欢花一样温和待人,播撒馨香,珍惜与每个人的同城之缘,因此不再孤单。
我真正如街边的合欢树一般在小城扎下根,是在成家之后。当年与妻结婚之时,正值盛夏,租住在城东一处小院的两间西厢房,巧的是,院中竟植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。树干粗壮,枝叶葳蕤,花开馥郁,满院飘香,笼着这座小院,笼着我们俩。在树下,搭棚做饭,摆桌吃饭,摇扇乘凉,静扫落花,捻花逗趣,度过了一年的美好时光。
房东说,这株合欢树是他父亲当年栽下的,几十年了,根深叶茂。人虽已逝,却将这树留给了后人。老人家是热爱合欢之人,更是谦恭和善之人,因高大的合欢树影响了邻居采光,老人家忍痛割爱,毅然砍掉了伸向邻居院内的那枝。树的伤疤还在,可几代邻里的和睦更在。
因这合欢,我和妻子恩爱有加;也因这合欢,与房东一家及左右邻居有了很深的情谊。以至于我们离开那院十几年,依然常在合欢花开的时节,回那里看看,看看如今的他们,想想当年的我们。
今年我要经常离开故乡,离开小城,在外工作一年。那日,妻子在微信中说:“街里的绒花开了,回来看吧!”我顿时心生欢喜,是时候回家看看了。
一朵一朵的合欢花已从故乡如小绒伞一般纷扬飞来,落在我的心上,绒绒的、粉粉的、甜甜的,还痒痒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