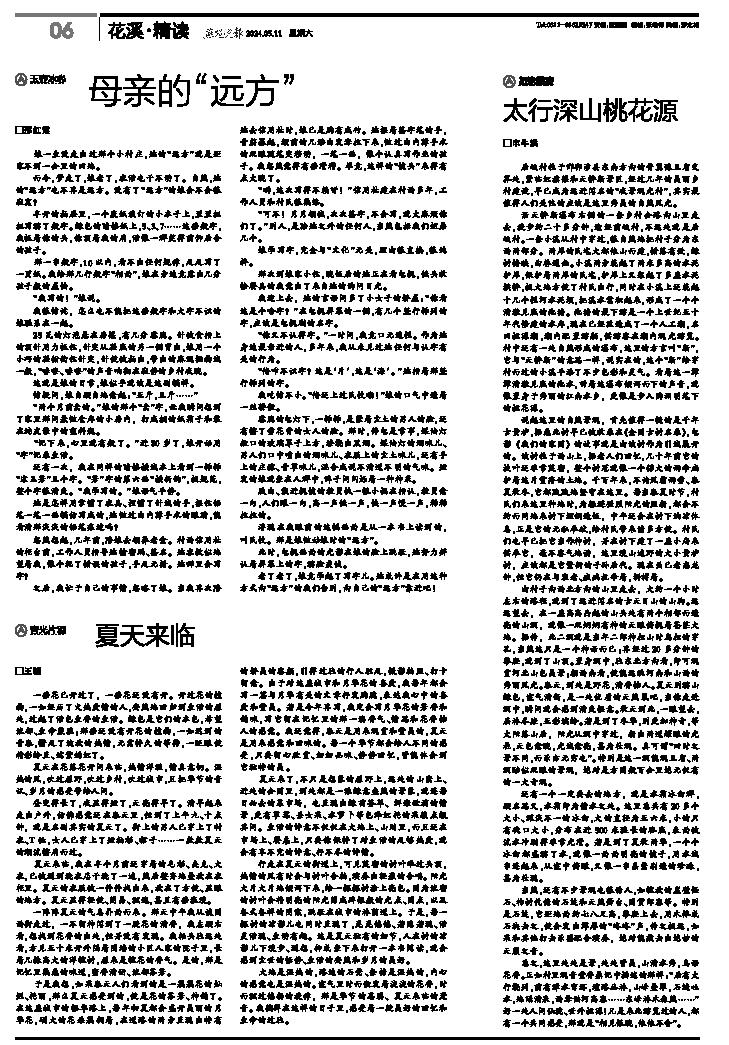□邢红霞
娘一生没走出过那个小村庄,她的“远方”就是距家不到一公里的田地。
而今,爹走了,娘老了,农活也干不动了。自然,她的“远方”也不再是远方。没有了“远方”的娘会不会很寂寞?
半开的抽屉里,一个废纸裁订的小本子上,歪歪扭扭写满了数字。绿色的暗格纸上,5、3、7……这些数字,我抵着你的头,你顶着我的肩,活像一群笑得前仰后合的孩子。
那一串数字,10以内,看不出任何规律,足足写了一页纸。我给那几行数字“相面”,娘在旁边竟露出几分孩子般的羞怯。
“我写的!”娘说。
我很惊诧,怎么也不能把这些数字和大字不识的娘联系在一起。
25瓦的灯泡悬在房梁,有几分朦胧。针被食指上的顶针用力抵住,针尖从鞋底的另一侧冒出,娘用一个小巧的鞋钳衔住针尖,针便被抽出,带出的麻绳抛物线一般,“哧嚓、哧嚓”的声音响彻在寂静的乡村夜晚。
这就是娘的日常,娘似乎就该是这副模样。
惊疑间,娘自顾自地念起:“五斤,三斤……”
“两个月前卖的。”娘的那个“卖”字,让我瞬间想到了家里那间兼做仓库的小房内,打成捆的纸箱子和装在蛇皮袋中的塑料瓶。
“记下来,心里就有数了。”近80岁了,娘开始用“字”记录生活。
还有一次,我在同样的暗格横线本上看到一排排“宋玉芳”三个字。“芳”字的第六画“横折钩”,极规范,整个字很清爽。“我学写的。”娘语气平静。
她是怎样用拿惯了农具、捏惯了针线的手,握住铅笔一笔一画模仿写成的,她做过白内障手术的眼睛,能看清那浅浅的铅笔痕迹吗?
忽然想起,几年前,陪娘去领养老金。村西信用社的柜台前,工作人员指导她输密码、签名。她求救似地望着我,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,手足无措。她哪里会写字?
之后,我忙于自己的事情,忽略了娘。当我再次陪她去信用社时,娘已是胸有成竹。她握着签字笔的手,青筋暴起,额前的几绺白发耷拉下来,做过白内障手术的双眼随笔尖移动,一笔一画,像个认真写作业的孩子。我忽然觉得有些滑稽。毕竟,这样的“镜头”来得有点太晚了。
“哟,这次写得不赖呀!”信用社建在村西多年,工作人员和村民很熟络。
“可不!月月领钱,次次签字,不会写,就太麻烦你们了。”别人,是除她之外的任何人,当然包括我们姐弟几个。
娘学写字,完全与“文化”无关,理由很直接,很纯粹。
那次到娘家小住,晚饭后的她正在看电视,低头收拾餐具的我觉出了来自她的询问目光。
我迎上去,她的言语间多了小女子的娇羞:“你看这是个啥字?”在电视屏幕的一侧,有几个竖行排列的字,应该是电视剧的名字。
“你又不认得字。”一时间,我竟口无遮拦。作为她身边最亲近的人,多年来,我从未见过她任何与认字有关的行为。
“俺咋不识字?这是‘片’,这是‘海’。”她指着那竖行排列的字。
我吃惊不小。“俺还上过民校嘞!”娘的口气中透着一丝骄傲。
朦胧的电灯下,一排排,是蒙着尘土的男人的脸,还有擦了雪花膏的女人的脸。那时,停电是常事,煤油灯敞口的玻璃罩子上方,缭绕出黑烟。煤油灯的烟味儿、男人们口中喷出的烟味儿、衣服上的尘土味儿,还有手上的庄稼、青草味儿,混合成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。短发的娘就坐在人群中,眸子间闪烁着一种神采。
肤白、戴近视镜的教员执一根小棍在指认,教员念一句,人们跟一句,高一声低一声,快一声慢一声,稀稀拉拉的。
浮现在我眼前的这幅画面是从一本书上读到的,叫民校。那是娘做姑娘时的“远方”。
此时,电视画面的光影在娘的脸上跳跃,她努力辨认着屏幕上的字,满脸虔诚。
老了老了,娘竟学起了写字儿。她或许是在用这种方式向“远方”的我们告别,向自己的“远方”靠近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