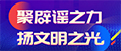□文/图 陈晔
2021年10月5日,连阴雨第四天,我回家探亲。在县城,我把东西放下,冒雨坐车到平阳镇,又从平阳雇车去一个叫“三将台”的小村。
雨一直没有停,也不见小。路边的枣树,枣儿落尽。
“正是该晒枣的时候,一下雨,枣全烂了。”路上和司机聊天得知,三将台没搬迁,我心里一块悬着的石头放下。我深怕因搬迁把老房旧屋拆了,我来是寻访孙犁先生足迹的……
寻访旧事
踏上这块热土,脑海里总会飘起那首优美深情的《索玛花开》。1931年,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来到阜平县平阳,他们从这片土地上走过。1937年,八路军又来这儿创建根据地,这次不仅仅是路过,而是常过、久住。住在这里的,除了战斗部队,还有文艺战士。这些文艺战士,有的成为享誉世界和全国的艺术家,孙犁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在多篇文章里提到平阳河、三将台。
我是来寻访孙犁先生旧事的。
“村里有没有住过八路军?”
在三将台村路边,几个女人听到我的问话后摇摇头。雨小了,她们走出家门在路边说话。
“1939年来过。”
“那我们更不知道了。那时,还没俺们哩。”她们友好地笑了。
村里人是热情的,只有上年岁的人才知道久远的事。
“问问村里上年岁的人吧。”
路边聊天的女人中,一位年轻些的跑回来:“问问我三姥娘。”
我随她走进路边一座小院。被她称作三姥娘的人90多岁,头发灰白,在屋内一张床上躺着。听到我的问话,她说来过。因为孙犁1939年到三将台村,在村里办过妇女识字班。按她的年岁来推算,她应该知道。
从这家小院出来,碰到一个中年男人,他回家去问他爹,他是长子。
另一位年轻女子带我到坡根儿找人,我问她是不是这个村的人,她害羞地说:“俺是这村的闺女,也是这村的媳妇。”她带我来到傍坡根儿的一座老房。院子里,老人的三儿子已经先到。一会儿,大儿子也来了,就是进村遇到的第一个中年男人。
老人87岁,名叫曹德金。
“八路军?见过,见过。这里有过报社,晚上屋子里嘀嘀响……问我,就问对啦,年轻人不知道。”
嘀嘀响的是电台,报社要接收新闻,夜深人静,没有电灯,报社的工作人员在马灯或油灯下写新闻。
那一年,老人还是小孩儿,他跑着玩时听见屋子里传出嘀嘀的响声。
“村里就我还知道。”是啊,80多年过去了,只有他还记得……
第二故乡
孙犁把阜平当作“第二故乡”,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,在安新县同口镇做小学教师的他投身革命,在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从事宣传工作。1939年,他奉上级指示到冀西山地,先后在晋察冀通讯社、晋察冀日报社、边区文协、华北联大工作。在阜平,他由一介书生投身于民族抗日事业,用笔作枪,成为一名真正的文化战士。
1939年春,他到阜平,被派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。晋察冀通讯社1938年底成立,驻地先是在城南庄。孙犁分在通讯指导科,对通讯员进行写作指导,主要是指导写信,多的时候,一天要写七八十封。他编写了学习材料《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》,在当时边区印刷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铅印出版发行。不少通讯员以此为“教材”开始新闻写作。
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阜平“山穷水恶、地瘠民贫”,老百姓吃糠咽菜,糠菜半年粮。他们则是每天三钱油、三钱盐,“菜汤里的萝卜条,一根赶着一根跑,像游鱼似的。有时是杨叶汤,一片追着一片,像飞蝶似的。(《吃饭的故事》)”每天吃不饱,睡老乡家土炕,没枕头褥子,连炕席也没有。
1939年秋,晋察冀通讯社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。
据孙犁先生文章记载,三将台村是十几户人家的小村,山村依坡而建。孙犁住的房子旧址就是曹德金老人带我去的。房址是在这儿,当年日本鬼子把房烧了,现在看到的房子也因没人住塌了。烟火熏黑的房檩在雨中趴在倒塌的墙体上。
孙犁在三将台编辑油印刊物《文艺通讯》。一位家是曲阳的梁同志管刻写、印刷、装订、发行,梁同志后来给他留下一件大衣。他还帮一位女同志在村里办识字班教识字。1940年,他在散文《识字班》中写了三将台:“山下的河滩不广,周围的芦苇不高。泉水不深,但很清澈,冬夏不竭,鱼儿们欢快地游着,追逐着。山顶上,秃光光的,树枯草白,但也有秋虫繁响,很多石鸡、鹧鸪飞动着,孕育着,自得其乐地唱和着,山兔麅獐,忽然出现,又忽然消失。”“我们在这里工作,天地虽小,但团结一致,情绪高涨……”
他写的是秋景。从三将台村流过的河叫平阳河,是阜平大沙河的一条支流,汇入王快水库。
我走到河边,看他笔下的平阳河。连续几天阴雨,河水涨了,两边地里种着白菜、萝卜,有的地方开着大片黄色的洋姜花。这里的人用洋姜腌菜,口感好,脆生。无疑这也是孙犁在时看到的秋天景色、物象。
他散步时,会走到河边附近的沟汊。村里的枣树、核桃、柿子树、黑枣树进入他的视野。
在三将台,他编刊物,也执行任务。不久,上级安排他去雁北作为战地记者执行任务。雁北是指山西和河北阜平交界的繁峙、应县一带。日军扫荡很凶。接到任务后,他从三将台出发去采访。深秋已冷,雁北更冷,他单衣不胜寒,因气候不适应病了,此行收获不大,仅写了一篇文艺通讯。
从雁北回来,快过春节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在外过年。因战争,不能回家。年根,他站在三将台高山上,想家和亲人。村里准备过年,做豆腐,推糕面,也请报社的同志写对联,新年气氛渐渐浓厚。腊八节,村里送来一筐红枣,他们生吃,还做了一顿阜平味的腊八粥。过年,村里给他们杀了只羊,拿出好吃的给他们,让他深受感动。
在三将台,孙犁住的坡根儿房子旁有盘石碾。如今石碾没了,碾盘还在,在路边靠着。孙犁经常看村里人推米面,那个年代吃的东西都是在碾上推的。
1940年,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阜平。
夏天的一天,孙犁正在三将台山坡上的一间小屋油印《文艺通讯》。诗人田间和邵子南来三将台看他。田间是晋察冀边区有名的抗战诗人,两人相见亲密握手。邵子南站在田间身后,穿一身军装,打着绑腿,赤脚穿着草鞋,走路矫健敏捷。邵子南在旁边大声说:“久仰——真正的久仰!”彼此早有所闻,很谈得来,他们相约互相走动。
邵子南所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距三将台不远,没事时,孙犁就沿河滩砂石路,逆河而上,去找邵子南。邵子南主编《诗建设》,用红绿色油光纸印刷诗传单。
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哪个村?我来这儿,也为考证这个村。据孙犁先生“沿河滩砂石路,逆河而上”三四里描述,询问了几位老乡,经他们核实,确定这个“沿河滩砂石路,逆河而上”的村应该是康家峪。据姓郑的老乡描述,这两个村之间有块芦苇地,很漂亮。孙犁在《识字班》中提到过。
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这里时条件很艰苦,四五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,只有一张桌子放钢板蜡纸,但收拾得很整洁。墙上整齐地挂着各人的手榴弹、书包,炕上摆着打理得整整齐齐、准备随时行动的被包和油印机,以及刚印好尚待装订的诗刊。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对孙犁非常热情。每逢他来,总是弄些好吃的招待他。他结识了周巍峙等当时的文艺界名人。
1940年7月,边区文协成立。孙犁调到文协,离开三将台。从来到走,他在三将台住了不到一年。1941年春节,孙犁随文协离开阜平,前往平山石鼓洞。1942年夏,孙犁由冀中返回阜平,依然在文协工作。1943年晚秋,孙犁从晋察冀日报社调到华北联大高中教书。第二年春,从繁峙回阜平,当即接到通知去延安。
温暖的回忆
自从离开阜平,他再未回来过。阜平在他心中打下很深的烙印,他以晋察冀边区为题材写下中篇小说《村歌》、小说《吴召儿》《石猴》《山地回忆》等,《山地回忆》入选中学课本。
他在阜平生活了五个春秋,一草一木,一山一石,都使他产生过深厚感情。“他由一个刚刚加入革命队伍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,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、革命作家(管蠡《孙犁传——走出荷花淀》)”。他忘不了阜平的山山水水,“阜平,在我们这一代,该是不能忘记的了,把它作为摇篮,我们在那里成长。那里的农民、砂石、流水、红枣,哺育了我们。(《亲家》)”“一个机关住在村里,住得很好,分不出你我来啦。过阳历年……村里呢,买了一只山羊,送到机关的厨房。到旧历腊八日,村里又送来一大筐红枣,给他们熬腊八粥。(《鲜姜台》)”这个“鲜姜台”,就是三将台。
在阜平和三将台的“禾场、河滩、草堆、岩石上”,他读鲁迅的书,读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屠格涅夫所有的长篇小说和爱伦堡的通讯。阜平和晋察冀是他文学艺术的摇篮,是他的“第二故乡”!
文章依旧在
国庆雨中行,我考证了孙犁先生在三将台时的一些细节,这些远远不够。
孙犁先生在平阳的时间是1939年和1940年,他在三将台时,三将台有一棵老黑枣树,在那个饿肚子的年代,这棵树上的黑枣他肯定吃过。善良的乡亲们不会不把黑枣送给在这里的八路军。这棵黑枣树前几年干枯了,村里人把它砍伐了。
在我采访的曹德金房前有道沟,沟里有俩土洞。鬼子扫荡时发现了这俩洞,藏着的报纸全被弄走了。虽然大“扫荡”时,孙犁先生住过的房子被烧毁,但那面坡还在,那条河还在,孙犁先生的文章还在。
从平阳到三将台,我是雇车去的。说好了价格,采访结束后,我又多给了司机20元钱。他说:“你给多了。”
我感谢他的雨中同行。
我知道,这次雨中采访意味着什么,我完成了先生的一个心愿。